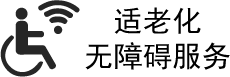涡口古城
涡口即涡尾,为涡河入淮处,俗称外河口。古时的涡口,既是军事要塞,又是交通枢纽。涡口城滨淮涡两水,北人欲占据江淮,必先占涡口。南人欲保卫江淮,必固守涡口。涡口的军事价值不亚于钟离(临淮关)、寿春(寿县)、楚州(今淮安市境内)。
东汉建安十四年(209年),东吴的周瑜举兵进攻合肥,曹操为夺取江淮之地,对抗东吴,亲率大军自谯(亳州)经涡河入淮。舳舻千里,旌帆如云,泊于涡口城外的涂山脚下。曹操之子曹丕与王粲各作一首《浮淮赋》。曹丕在《浮淮赋》序文中说:“王师至谯东征,大兴水军,泛舟万艘,时予从行。始入淮口,行泊东山,睹师徒,观旌帆,赫哉盛矣。”其赋中有“浮飞舟之万艘兮,建千秋将铦戈”。
王粲的《浮淮赋》中有“背涡浦之曲流兮,望马邱之高澨”、“群师按部,左右就队。轴轳千里,名卒亿计”等语。此后方演出了曹军屯住合肥,张辽大战逍遥津等故事。
三国魏黄初五年(224年),魏文帝曹丕以舟师沿涡河至涡口,再次入淮。建衡二年(270年),吴末帝孙皓,曾派大将丁奉入涡口,与建立不久的西晋对抗。
南北朝时,涡口亦为主要军事城堡。清嘉庆《怀远县志》载,南齐永泰元年(498年),豫州刺史裴叔业,领军攻打北魏占领的涡阳和龙亢,后来北魏援军铺天盖地而来,眼见败局已定,裴叔业主动放弃龙亢,连夜东撤全力退保涡口。
大运河贯通南北后,涡口仍为国家漕运的咽喉要道之一。唐贞元年间,唐德宗在叛军扼控运河之后,为了确保涡河漕运通畅,在涡口两侧各筑了一座城池。从此,唐几任濠州刺史均兼任涡口城的守备使。五代十国,战事不断。后周显德三年(956年),周世宗柴荣为控扼淮涡水运,令军士在涡口两城间架设浮桥,并于此设“镇淮军”。涡口两城成了镇淮军屯兵之地,故又有拖城之称。
清嘉庆《怀远县志》大事记载:后周显德三年(956年)二月,南唐兵万人营于涂山之下,与后周军对峙。柴荣命赵匡胤击之。赵设计佯败,布下伏兵,南唐军战舰追到涡口,突然号炮三响,震天动地,埋伏在涡口的后周水陆大军仿佛从天而降,南唐军被团团围住,其监军何延锡等将领被斩下头颅。此战,后周军大获全胜,夺得南唐军战舰50余艘。
谋江淮者必占涡口。牢牢控制了涡口城,进可攻,退可守。显德五年(958年),后周终于夺取了沿淮的濠州、楚州、寿州等地,掌握了对江淮地区的控制权。这也为后来赵匡胤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,代周为宋,兵峰南指,奠定了基础。北宋一统山河,涡口作为中原水上交通枢纽和商贸重镇,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宋人欧阳修,乘船过涡口城,留有诗歌《涡水龙潭》。
宋人梅尧臣过涡口城,留有《涡口》、《涂山》、《咏卞和》等诗。他在《涡口》中说:“秋水见滩底,浅沙交浪痕。白鱼跳处急,宿雁下时昏。带月移涡尾,落帆防石根。”宋人苏东坡舟泊涡口城,留有《十二月二日将至涡口五里所遇风留宿》、《淮上早发》、《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》、《濠州七绝·涂山》等诗。
北宋灭亡,南宋朝廷偏安江南,与金人隔淮对峙,涡口成为边关要塞。金兵南下,屡犯涡口。宋金两国多次在涡口鏖战。嘉定十二年(1219年),宋军滁濠光三州京东总管李全在金军大举南下之际,率军夺取涡口,切断金兵退路。李全继而与金都监纥石烈牙吾答、驸马阿海等战于涡口和涂山东南的化陂湖,大败金兵,斩杀金将数人。
涡口地名变迁,还与南宋朝廷和黄河有关。南宋建炎二年(1128年),宋高宗赵构的东京(开封)留守杜充,为阻金兵南下,在滑州掘开黄河大堤,黄河洪水奔腾咆哮,经泗水夺淮入海。淮河下游泥沙淤塞,水流不畅,涡口城遭洪水冲击而毁坏。南宋宝祐五年(1257年),丞相贾似道上奏朝廷:“涡口上环荆山,下连淮岸,险要可据。”理宗皇帝御答:“荆山为城,义在怀远。”于是将原来的镇淮军改为怀远军,又在涡口城设怀远军管辖的荆山县。从此,涡口之名被荆山、怀远所取代。
涡口城的地名虽然消失,但是,它作为战略要地依然存在。明建文四年(1402年),燕王朱棣率军“靖难”,曾从涡河顺流而下,东达涡口入淮,再进攻沿淮城镇。清光绪以来,涡口作为淮河重要关口,驻有清军水师,并配有炮船、哨船。1911年,津浦铁路修建后,蚌埠兴起成市,涡口(怀远)等沿淮古城的地位逐渐弱化。但涡口作为古城戍、古地名和自然景观,仍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。明末清初,古涡口变成了绿野良田,西移的涡口南北两岸相继建起了顺河街、屾河街(林家圩子)。因涡淮洪水泛滥和日寇入侵,屾河街最终成为瓦砾。顺河街也饱受洪水之苦。2003年洪水过后,移民建镇工程启动,至2008年底,顺河街居民陆续搬迁到涡北移民新区。今日的涡口,河道通畅,彩虹飞架。桥上铁马奔驰,桥下千帆竞发。涡口两岸已经成为滨水生态保护区和居民休闲游乐园。
 中国政府网
中国政府网 皖公网安备34032102100001号
皖公网安备34032102100001号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
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